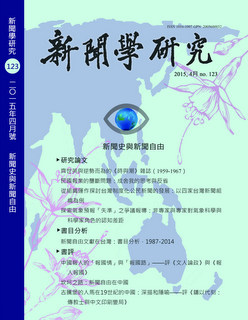保林杰(Leo Bollinger)是公法學者,曾經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、任內大力改革該校新聞教育。他說,「消極與積極自由這兩個概念,可以結合成軛……消極自由這個領域的建立,適足以成為來源或方法,得以讓人爭取積極自由」。
保林杰認為,在哲學家柏林(Isaiah Berlin)筆下,積極自由常墮落為專制或威權國家的鎮壓工具。果真如此,強調人有免於動輒得咎的消極自由,就與積極自由呈現敵對之勢。但保林杰這位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專家,多年來的論述重點之一,就在表述,消極與積極新聞自由,不但可以,並且應該是互補的。
根據陳鴻嘉與蔡蕙如的整理,台灣解嚴當年迄至去(2014)年底,在台灣出版或宣讀有關「新聞自由」的碩博士論文、期刊、圖書與研討會論文,總計達362筆。兩人從中抽樣檢視30筆,「發現多數文獻中的新聞自由屬消極意義,積極新聞自由之論述較少」。
放在歷史發展過程,新聞自由的重要面向之一,既然是用以掙脫王權的束縛;既然新聞自由的主張是,我群通過物質化的言論,對外紀錄見聞與表述觀點時,無須得到政府的授權,也不能任意遭致限制,那麼,政府鬆手、免除或最小管制,往往也就等同於新聞自由,實屬可以理解之事。
不過,掌握公權力的國家機器在鎮壓自由時,相關人究竟怎麼具體應對,有待細描。邱家宜寫就的〈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《時與潮》(1959-1967)〉,交待的正是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在1960年9月被勒令停刊、一年後《公論報》產權易手,而康寧祥等人的《台灣政論》(1975)尚未短暫浮現之前,非執政黨人士在威權陰影下,行使新聞自由的艱辛與快意。當時,即便早在1960年,《時與潮》已報導,國民黨中常委、主導文宣政策的陶希聖「多次親口」說,成舍我在北京的《世界日報》獲得許可,出版為《台灣世界日報》,可以「樂觀其成」,最後「上峰」卻封殺照舊。《時》本身則在7年後,因報導監委及立委涉入「油商賄案」遭警告後,並不退縮而是予以反擊,直至最終自行停刊。
甲午戰爭後,成舍我與齊世英誕生。毫無疑問,成、齊兩人體現了「中國現代報刊的主流」傳統,他們具備了吳廷俊與於淵淵述及的類型,具有「報國情」,進而通過報刊進入「報國路」。吳、於指出,李金銓主編的兩本書,《文人論政》(2008)以及書名取自成舍我題詞的《報人報國》(2013),已「在新聞傳播學界引起強烈迴響」。兩書所提供的26篇論文,不僅是「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」,「而且是……最應該有的『讀法』」。
在國民黨來台以後的三、四十年間,受限於時代所設定的框架,真誠論事的報人或學人,若是因為其所眼見的政府,只存鎮壓角色,致使僅能看到新聞的消極自由,並無不合理之處。惟成舍我七、八十年前對於報業的觀察與思維,已有超越時代侷限的性質。成氏的這個見識,至今少見人發明,直至黃順星這篇〈民國報業的壟斷問題:成舍我的思考與反省〉,方予正視,還原並發揮於當前。
歷來,對於成舍我的描述,不乏以渠為「托拉斯、深諳印刷資本主義之道、成功的企業(家)」,或將其個人思想歸入「受無政府主義影響」。黃順星獨排眾議,發覺、提醒並強調,早在1930年,成於倫敦考察,就在寄回中國發表的評論說,「不願未來……的中國新聞事業」,出現類如當時英國Beaverbrook與Rothermere之類,「以報紙公器鼓動政潮」、「辦報……惟在……增加廣告收入」的報閥。到了1932年,他已察覺商業化的報紙「無法成為文人發聲倡議的工具」,中國即將「和歐美一樣……文人……(不能與)資本家競爭……只好拱手讓人」。既然看到「資本化報業市場的弊端」,成舍我的「報業發展藍圖」,從其發表於1932至1944年間的文章,可以四句話概括:「資本家出錢,專家辦報,老百姓說話,政府認真扶助、依法管制」。對於報人的歷史領悟,黃順星以當前的話語,總結其建言方向,就在「公共化之必要」。
傳媒若能公共化,如同人之神經與血液循環系統健全,價值不言而喻,但公共化有其困難,其一是公權力若欠缺認知,能力不足,或歷史窠臼與包袱尚未解除,就會出現進一步退一步的現象,不容易讓民眾看到明確的方向與改進的曙光。人們不滿意傳媒現況,公權力的規劃績效不彰,遂有「自力救濟」之舉。
台灣的「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」在前(2013)年底成立,德國之聲中文網當時曾予報導,指「獨立媒體正在改造台灣社會」,因為他們資源雖少,但具有「批判精神,容易打破政商勢力的箝制」。林宇玲選取的4個「公民新聞組織」,從2012年8月起,以一年時間訪談12位記者與管理者,試圖理解這些組織的創辦定位、所有權形態、經營財政來源及人員多寡,會與其表現產生哪些聯繫。作者說,她所選取的4家平台,都認同公民記者的表意自由,但實際上,一旦其影音圖文的表述進入專業領域,必然仍會涉及編輯的控制過程。惟若從另一個角度審視,則本文稱之為公共模式的「PeoPo公民新聞台」(7位公視員工輪任編輯),另類模式的「上下游新聞市集」(8人全職)、取廣告作為主要財源的獨立媒體「新頭殼」(10位員工),以及商業媒體「今日新聞網WEnews」(2位專職編輯),其實都有獨立記者的身影。
但新聞人的認知、傳媒經營與產權及財政的公共化,固然符合社會所需,亦能在較為相對充分的水平,提供資源讓新聞人發揮質量更高的積極新聞自由,遂行報導與調查,提供較為妥適的告知、預警、協調與糾惡揚善等傳媒職能,但是,這並不能保證其所傳播的內容,盡如人意。
2009年3月,義大利負責預測與預防重大災害的「民事環境保護署」副主任Bernardo De Bernardinis表示,儘管當時L’Aquila市已經連續4個月出現系列震動,但附近應該「沒有危險」。他甚至對當地電視台的記者說,「事實上科學社群告訴我,地牛的這些微顫是好事情,因為可以持續釋放能量」。6天後,該城與附近許多村莊成了廢墟:6.3級地震來襲,數以千的計建築物毀壞,308人死亡。地震後,檢察官以過失殺人罪起訴該署7個人。2012年,7人各遭判刑6年,引發全球科學家譴責這是荒謬審判,因為地震無從可靠地預測,判例將「使任何提供科學建議的人噤若寒蟬」。2014年底,經上訴,6人無罪開釋,但De Bernardinis仍然入罪,只是刑期減至2年。
5個月後,台灣發生「八八風災」,包括高雄小林村遭土石流活埋的亡者,共有699人罹難,氣象預報是否「失準」以致造成災難,同樣成為政府與民眾等非科學家的咎責對象。江淑琳記錄並分析了這個過程,她蒐集2009年8月起,迄至10月底監察院糾正氣象局為止,4家綜合報紙與唯一晚報有關八八風災的報導與評論,佐以中央社與其他政府材料。作者提醒,這些媒體一方面具有「平台」的功能,有關氣象報導是否「失準」及其爭論固然在此進行,但媒體同時也是「建構者」,其本身的報導與評論方式及內容,影響了民眾對災難的感知。
本期另有2篇書評,分別介紹蘇精的《鑄以代刻: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》,以及孫旭培的《坎坷之路:新聞自由在中國》。
在卞冬磊看來,蘇精一書儘管「未涉理論」,但運用第一手史料「嫺熟,敘事細密,翔實可靠」,是「禁得起時間考驗的力作」,足以帶領讀者認識「19世紀初到70年代……基督……新教傳教士引介西方活字,革新中文印刷的歷史過程」。
劉海龍說,撰寫中國文人爭取新聞自由的「坎坷之路」,「最合適的人選」無疑是曾經參與新聞法制訂過程、至今撰述不歇的孫旭培。孫氏一方面要「揭開把沒有自由說成無產階級自由的奧秘」,他方面則要指認,中國傳媒在1980年代逐漸市場化,至今難以遏止,致使新聞自由「未有明顯」增進,也是事實。劉海龍認為,孫旭培不同流合污,難能可貴而對後輩已有示範與啟發之餘,卻專注於論戰與說服「權力菁英」,反而忽略了「新聞工作者」與其他體制內外的力量,或許仍有可觀之向下結合,以求擴大新聞自由空間的機會。
馮建三
2015/4/13